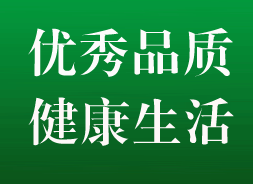大环内酯类药物的免疫调节是重症潜在的治疗
大环内酯类药物的免疫调节是重症潜在的治疗方向
ReijndersTDY,SarisA,SchultzMJ,etal.Immunomodulationbymacrolides:therapeuticpotentialforcriticalcare.LancetRespirMed.;8(6):-.doi:10./S-(20)-1
1.简介
危重患者普遍存在免疫功能失调。脓毒症加重这种失调,微生物表达的病原微生物相关分子组(pathogen-associatedmolecularpatterns,PAMPs)和损伤相关分子组(damage-associatedmolecularpatterns,DAMPs)从损伤组织中释放,通过和分子识别受体如Toll样受体(Toll-likereceptors,TLRs)和Nod样受体(Nod-likereceptors,NLRs)等结合,启动强烈的炎症反应,导致器官衰竭。与过度炎症反应伴行的免疫抑制和耗竭,使患者易于出现继发感染和潜伏病毒的再活化。其他重症如ARDS、多发伤和重症急性胰腺炎等,也产生相似的免疫反应。初期反应幸存的患者常合并严重的长期免疫功能紊乱,如持续炎症,免疫抑制和分解代谢,也就是ICU后综合征(post-intensivecaresyndrome)。但尽管经过30年的研究来调节和控制免疫失调,目前还没有进入临床的治疗措施。
大环内酯内药物是一组抑菌抗菌药物,通过和细菌核糖体结合抑制蛋白质合成,对多种革兰阳性和部分革兰阴性细菌具有活性。红霉素是一种大环内酯类药物,是胃动力素受体激动剂,少量给与可以减轻胃肠道的无动力。值得注意的是,大环内酯类药物具有强力广泛的免疫调节潜力,不仅仅通过简单的抑制或兴奋而调节免疫反应。大环内酯类药物似乎可以加速免疫稳态的恢复,保持甚至增强抗菌药物的作用。大环内酯类药物免疫调节效应最显著的一个例子来自于泛支气管炎,一种特发性的细支气管进行性破坏性病变。每日应用红霉素将其由致命性的病变转变为可治疗病变。此外,其对慢性气道病变如COPD、囊性纤维化和支气管扩张等累积的有益证据显示,大环内酯类药物具有治疗危重患者免疫功能失调的潜在作用。
ICU内免疫调节的策略在近30年开始受到重视,但仍没有有效的疗法。
2.重症患者模型
大环内酯类药物免疫调节的潜力在很多临床前模型如肺炎、脓毒症和肺损伤中研究。结果概括如下,大环内酯类药物单用,或与其他抗菌药物联合,可以有效治疗病原微生物,调节免疫反应,减轻炎症相关的组织损伤,改善生存,而与细菌负荷无关。在其他急性全身炎症情况下大环内酯类药物的使用研究很少,尽管最近Weis等的研究在蛙皮素(ceruletide)诱导急性胰腺炎模型中没有显示阿奇霉素的益处,可能是由于疾病的严重程度较轻。
在盲肠结扎穿刺模型中(肠道脓毒症,主要为大环内酯类耐药),与单用头孢类药物(ceftriaxone)相比,阿奇霉素联合头孢类药物使小鼠的生存率加倍,尽管两组动物血液中细菌的负荷相似。阿奇霉素降低治疗过小鼠血浆和肺中促炎因子如(IL-1β、IL-6,和TNF-α的浓度。在小鼠MDR鲍曼不动VAP模型中,接受阿奇霉素治疗的小鼠几乎都存活(n=22),而未治疗组仅不足半数存活(n=11)。阿奇霉素的保护作用表现在小鼠肺中炎症浸润细胞显著减少。在呼吸机相关肺损伤模型中进一步研究了大环内酯类药物肺保护的效果。与左氧氟沙星或空载对照相比,克拉霉素减轻肺损伤和中性粒细胞浸润。
3.危重患者的临床研究
研究大环内酯类药物对急症患者免疫调节效果的研究很少。已完成的研究主要是回顾性和观察性研究,与临床前研究相似,主要是关于肺炎、脓毒症和肺损伤(表)。考虑免疫通路与危重患者的临床亚型有重叠,报道的受益可能与其他免疫失衡疾病相关,如重症胰腺炎、多发伤和烧伤等。
3.1肺炎
在细菌性肺炎中,局部炎症对于清除侵入的病原微生物非常重要,但炎症不受控制则导致肺损伤、ARDS和脓毒症。观察性研究中合并过度炎症反应危重患者受益于大环内酯类药物药物,病死率下降,可能是由于免疫调节作用,或其他非抗菌药物相关效果。在社区获得性肺炎(CAP)治疗72h无好转的患者,与接受其他抗菌药物方案相比,接受大环内酯类药物治疗的患者支气管肺泡灌洗液中细胞因子(IL-6,和TNF-α)浓度低,达到临床稳定的时间短。在β内酰胺药物基础上加用大环内酯类药物治疗中-重度CAP的有效性还没有定论。
大环内酯类药物治疗效果最明显的是肺炎球菌肺炎,一种最常见的CAP,不管致病微生物是否为大环内酯类药物耐药。可能是由于抑制了肺炎球菌溶血素(pneumolysin),或刺激脾巨噬细胞清除了细菌。
大环内酯类药物能抑制群体感应(quorumsensing),即细菌在数量减少后增加毒力的一种机制。一项RCT研究阿奇霉素是否通过抑制定植的大环内酯类药物耐药的铜绿假单胞菌的群体感应,从而预防VAP。研究者发现与对照组相比,阿奇霉素处理后的患者VAP发生率下降,但没有达到统计学显著差异。当vanDelden等仅分析产鼠李糖脂(rhamnolipids)的铜绿假单胞菌后发现,对照组5/5发生VAP,而阿奇霉素组1/5发生VAP。而另一项关于铜绿CAP的观察性研究,没有发现有生存获益。
3.2脓毒症
在脓毒症时,全身感染导致严重的免疫失调在原发感染已经清除后,仍然持续很长时间。在肺炎相关脓毒症中,即使培养的病原微生物对大环内酯类药物耐药,应用大环内酯类药物药物治疗可以改善30d和90d生存期。在一项小样本回顾性研究中(n=),应用阿奇霉素治疗(n=29)的机械通气脓毒症患者的机械通气时间缩短。
Giamarellos-Bourboulis等进行的2项RCT评估了克拉霉素治疗脓毒症的免疫调节效果。为了排除抗菌素的抗菌效应相关生存益处,研究者仅入组大环内酯类药物耐药的病原微生物感染。第一项RCT入组例VAP患者,第二项RCT入组例可疑或微生物证实的革兰阴性脓毒症患者(肾盂肾炎、腹腔脓毒症,或原发性菌血症)。尽管2项研究的主要终点(28d病死率)均为阴性,克拉霉素减少症状持续时间4-5.5d。与其他观察性研究一致的是,克拉霉素对于危重患者效果最好。第一项研究中,克拉霉素组因脓毒症休克和多器官衰竭死亡的风险低于对照组。在第二项研究中,在54例休克和多器官衰竭患者中,克拉霉素组病死率54%(15/28),对照组病死率73%(19/26)。
在第一项研究的二次分析中,在随机化后D4,接受克拉霉素治疗的VAP合并脓毒症患者血清IL-10/TNF-α比值下降,而其单核细胞显示在脂多糖刺激后IL-6升高,TNF-α水平下降,共刺激因子CD86水平增加。
这些结果提示克拉霉素可以逆转免疫抑制和内毒素耐受,加速稳态的恢复。对于相同研究的再次分析发现,与28d病死率相比,克拉霉素组90d病死率显著下降。总之,这些资料提示大环内酯类药物有助于从免疫抑制恢复稳态,维持固有免疫细胞功能,对抗侵入的病原微生物。
3.3ARDS
肺炎、脓毒症或其他局部和全身病变可以升级为ARDS。在一项RCT的二次分析中(n=),大环内酯类药物与d病死率下降和机械通气时间缩短相关。在这项研究后,日本的一个中心对于ARDS采用阿奇霉素辅助治疗,报道了相似的结果,尽管研究为前后对照,且时间跨度长(4–17)。在一项例ARDS的研究中,例接受大环内酯类药物作为非抗菌原因,结果发现有生存获益。在倾向配比亚组分析中,这种效果仅见于非肺源性ARDS且无过度炎症反应亚型的患者。在一项阿奇霉素治疗革兰阴性脓毒症的RCT中,阿奇霉素(n=35)和对照组(n34)均合并ARDS,病死率分别为28.5%和55.9%。相反,最近例急性呼吸衰竭(包括ARDS)的研究中,例接受大环内酯类药物作为抗菌目的,结果与对照组在病死率、机械通气时间或继发感染率方面无显著差异。
4.与重症相关的作用机制
尽管大多数大环内酯类药物免疫调节的体内研究与肺炎症相关,大环内酯类药物的细胞效应提示可能影响肺外炎症。图1显示大环内酯类药物在肺感染时的临床效应。
图2显示各种免疫细胞类型的效应。
这里主要探讨14元环和15元环的大环内酯类药物,如阿奇霉素、克拉霉素和红霉素,因为免疫调节作用主要以上述药物研究,而不是16元环如交沙霉素(josamycin)。一些效应来自对靶细胞的直接修饰,另一些效应来自复杂的全身交互反应,如小鼠的肠道菌群在应用一剂大环内酯类药物后的改变维持较长时间,这会继而调节免疫反应。此外大环内酯类药物还产生非免疫效应,增加气道对病原微生物的防御效应,如改变痰的粘稠度,降低其过度分泌,增加气道上皮的完整性,降低类十二烷酸的代谢。
4.1对炎症反应启动的影响
在危重患者,DAMPs和PAMPs通过与组识别受体如TLRs相互作用诱导强力的免疫反应。大环内酯类药物降低树突细胞和巨噬细胞表面的TLR表达,而不影响中性粒细胞或淋巴细胞。重要的是,大环内酯类药物通过多种机制消弱TLR通路,可以是其免疫调节的主要机制(图3)。
4.2对细胞因子、趋化因子和趋化效应的影响
TLRligation(?)活化免疫细胞,清除侵入的病原微生物。但危重患者出现过度炎症反应,特征是过度释放促炎细胞因子。大环内酯类药物通过减少促炎细胞因子释放和限制免疫细胞迁移,从而减弱这种反应。大环内酯类药物减少气道上皮细胞、单核细胞、巨噬细胞、树突细胞和T细胞产生IL-6和TNF-α。同样,大环内酯类药物消弱NOD样受体蛋白3(NLRP3)和NLRC4炎症体的活化,减少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在接受脂多糖或细菌刺激后IL-1β的产生。在革兰阴性和革兰阳性细菌感染模型中,大环内酯类药物减少血清和支气管灌洗液中IL-1β,IL-6,和TNF-α的量。大环内酯类药物抑制树突细胞IL-12的产生,可能解释为什么其能减少T辅助细胞-1的作用,减少T辅助细胞-1产生IFN-γ。
大环内酯类药物对抗炎因子的作用不明确。大环内酯类药物可以通过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上调IL-10,但是抑制T细胞和树突细胞的IL-10产生。在鼠感染模型,大环内酯类药物增加血清或支气管灌洗液IL-10的含量或无影响。某些研究中观察到IL-10增加,部分原因是大环内酯类药物诱导髓细胞衍生抑制细胞(myeloid-derivedsuppressorcells,MDSCs)。最近研究显示,在致命休克(注射脂多糖诱导)和流感后肺炎球菌肺炎模型,IL-10对于保护克拉霉素诱导MDSCs至关重要。
危重患者的过度炎症可以导致大量白细胞募集。这个过程导致血管渗漏和组织损伤,最后出现器官衰竭。鼠急性感染和呼吸机肺损伤模型中,给与大环内酯类药物可以减少肺内白细胞,特别是中性粒细胞的募集,预防对肺的破坏。生长因子和趋化因子浓度的减少可以解释这些结果。总体上,无论体外和体内,大环内酯类药物减少粒细胞-和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的产生,下调募集粒细胞、单核细胞和其他白细胞的趋化因子,如IL-8(CXCL8),巨噬细胞炎症蛋白-2(macrophageinflammatoryprotein2,CXCL2),和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CCL2)。而且,大环内酯类药物体外减少CD4+产生IL-17,可能进一步减弱中性粒细胞的活化和移动。
4.3对细胞增生和分化的影响
除了向感染部位募集,免疫细胞也增加以控制感染。但危重患者的免疫反应常受过度炎症和免疫耗竭影响。大环内酯类药物通过同种树突细胞或通过α-CD3与α-CD28结合,抑制CD4T细胞增殖,而减轻过度炎症反应。首先,大环内酯类药物下调抗原呈递细胞共刺激分子的表达,阿奇霉素在体外可以减少树突细胞主要组织相容复合体(MHC)II的表达。这种下调,以及促炎因子产生的减少,可能减少T细胞增殖的刺激。第二,暴露于阿奇霉素处理过树突细胞刺激的T细胞产生较少的IFN-γ,以及较多的IL-10,从而减弱自分泌活化以及其后的细胞增殖。细胞活力的减弱可以解释增殖减少,因为报道高浓度的大环内酯类药物可以诱导T细胞凋亡。
大环内酯类药物还通过使细胞分化表现为更耐受原性的表现型而减弱危重患者的过度炎症反应,表现为暴露于大环内酯类药物抗原呈递细胞刺激的T细胞释放更多的抗炎因子IL-10,并向T辅助细胞-2分化,而不是向T辅助细胞-1分化。大环内酯类药物在体外和体内还使巨噬细胞和单核细胞表现为耐受原性或M2样表现型。最近研究显示克拉霉素治疗增加小鼠脾和肺MDSCs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的数量,研究显示克拉霉素治疗还增强人类循环中MDSCs。在鼠致命的脂多糖诱导休克和流感后肺炎球菌模型中,这些MDSCs可以减少促炎因子释放,减弱炎症相关组织损伤,改善生存期。尽管这些效应对合并过度炎症反应的患者可能有益,但对于免疫耗竭的患者可能有害。
4.4对生存的影响
危重患者合并T细胞、B细胞、树突细胞和巨噬细胞过度凋亡时,可能导致院内感染,出现多器官衰竭和死亡。相反,危重患者的中性粒细胞凋亡减少或不受影响,可能延长炎症反应。大环内酯类药物通过直接刺激凋亡,或抑制促生存分子如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的释放,缩短中性粒细胞的生存。这种促凋亡效应不一定损害对抗病原微生物的防御反应。一项研究显示,存在肺炎链球菌时,阿奇霉素没有导致中性粒细胞凋亡。高浓度阿奇霉素在体外诱导树突细胞、自然杀伤细胞和CD4T细胞的凋亡。但在临床使用浓度下没有发现这些细胞的凋亡,因为对危重患者不会产生免疫抑制。
4.5对细胞功能的效应:吞噬作用、胞葬作用和杀菌
吞噬作用(phagocytosis)使细菌内化可以防止播散,便于杀灭,对于呈递抗原启动适应性免疫是必须的。危重患者的吞噬能力较健康人群差,导致院内感染和死亡。大环内酯类药物增强树突细胞和肺泡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但红霉素不增加中性粒细胞对化脓性链球菌的吞噬作用。阿奇霉素可能改善体弱患者的免疫细胞功能,如阿奇霉素可以恢复COPD患者肺泡和单核衍生的巨噬细胞消失的吞噬能力。
为了帮助炎症后的组织修复,通过胞葬作用(efferocytosis)清除死亡和损伤的细胞,这种机制与吞噬作用相似。ARDS时胞葬作用受损。大环内酯类药物在体外和体内通过巨噬细胞和树突细胞增强胞葬作用。
为了在吞噬细菌后进行有效杀灭,需要通过吞噬溶酶体靶向细菌。吞噬溶酶体的酸化和吞噬体的高度稳定性对于此过程至关重要。吞噬体受高度氧化应激的影响,因为呼吸爆发常杀死细菌,导致溶酶体膜的渗透作用。体外或体内应用阿奇霉素治疗,通过保护巨噬细胞免受氧化应激相关的溶酶体泄露和其后的细胞死亡,从而改善吞噬体的稳定性。吞噬体稳定性增加后可以防止细菌逃离吞噬体,从而有助于清除细菌。
自噬(Autophagy)是细胞用于清除不必要的或无功能的细胞成分,也可以杀死病原微生物,调节免疫反应,防止凋亡。脓毒症早期自噬增加,帮助清除病原微生物,但是后期自噬受抑制。阿奇霉素治疗可以增加自噬溶酶体的稳定性,防止酸化,后者可以损害自噬溶酶体的成熟和后续降解。
报道大环内酯类药物增加吞噬体内病原微生物的杀灭。总体上,根据杀灭特异病原微生物所需的通路,大环内酯类药物可以增强或抑制病原微生物的杀灭。一个典型的机制是呼吸爆发,受大环内酯类药物以时间依赖性和环境依赖性的方式影响。大环内酯类药物通过初级中心粒细胞抑制自发性和N-甲酰甲氧基-亮氨酸-苯丙氨酸(N-formylmethionyl-leucyl-phenylalanine)刺激相关的活性氧化物(reactiveoxygenspecies,ROS)产生,通过巨噬细胞增强金葡菌刺激相关ROS的产生。阿奇霉素在体外和体内抑制巨噬细胞内脂多糖诱导的一氧化氮(NO)产生和诱导性NO合成酶的表达,通过MDSCs增强自发性NO产生。
中性粒细胞有一个独特的策略缠住细胞外的细菌,中性粒细胞陷阱(neutrophilextracellulartraps,NETs)是通过中性粒细胞排出的DNA形成,抗菌药物肽可以对其进行修饰,这个过程称为中性粒细胞陷阱形成(NETosis)。脓毒症患者的NET形成增加,与器官功能不全相关。大环内酯类药物对于NET释放程度的影响不定。尽管大环内酯类药物可以抑制NET释放,也可能对自发性NET释放无影响。大环内酯类药物治疗过的中性粒细胞,其释放的NET显示抗菌药物肽修饰增加,意味者NETs的细菌杀灭能力更强。
为了杀死侵入的病原微生物,中性粒细胞还分泌各种抗菌药物肽,储存于细胞内的颗粒。大环内酯类药物在体外和体内刺激中心粒细胞降解。相反,红霉素可以结合并抑制弹力酶,后者是中性粒细胞释放的一种强力蛋白酶。报道克拉霉素可以降低弹力酶活性,增强髓过氧化物酶活性。但大环内酯类药物治疗可以降低脂多糖刺激后和呼吸机肺损伤后肺内的髓过氧化物酶浓度,可能是继发于中性粒细胞内流减少。阿奇霉素还通过自然杀伤细胞抑制穿孔素的表达,阻碍自然杀伤细胞活化和杀伤能力。最后,体内应用阿奇霉素降低了CD4和CD8T下表内颗粒酶B的浓度。
4.6抗菌效应外的细菌杀伤效应
除了通过抑制细菌蛋白合成来直接抑菌外,大环内酯类药物还通过几种机制减弱细菌的毒力。他们通过肺炎球菌抑制帮助细菌免疫逃逸的酶(LytA)的释放,即使该菌株对大环内酯类药物耐药。然后LytA下调肺炎球菌溶血素(pneumolysin),增加不提沉积,利于细菌杀灭。大环内酯类药物还通过其他细菌如大肠埃希菌、假单胞菌和真菌等抑制毒素因子的产生。在有利的生长环境下,细菌产生生物膜,降低其对抗菌药物和免疫细胞的敏感性和暴漏。生物膜是ICU内导管和医疗设备内定植的关键机制,因此是住院获得性感染的重要因素。大环内酯类药物通过假单胞菌、流感嗜血杆菌和表皮葡萄球菌减少生物膜形成,部分通过降低群体感应。最后,大环内酯类药物抑制细菌粘附于气道上皮。
5.新的肺抗菌大环内酯类药物衍生物
对加重抗菌药物耐药性的顾虑,阻碍了大环内酯类药物非抗菌治疗适应证的广泛应用。幸运的是,可以修饰大环内酯类药物以去除其抗菌效果,保留或增强其免疫调节能力。EM是一种非抗菌效应的红霉素衍生物,可以改善单胞菌气道感染小鼠的生存,可能是由于减少了促炎因子的释放。红霉素衍生物EM抑制感染诱导的促炎因子产生,NFκB活化,以及与红霉素相似程度的抑制上皮细胞粘液产生。EM通过增加CCL2分泌,增加肺内的F4/80+巨噬细胞计数,降低鼻病毒感染的病毒负荷,改善肺炎球菌感染的预后。阿奇霉素的非抗菌衍生物CSY降低小鼠肺内脂多糖诱导的促炎因子浓度。
大环内酯类药物还可以与其他分子如激素、抗菌药物肽或小的信号分子合用,增强它们的效果。因为大环内酯类药物体内相对稳定,聚集于吞噬细胞内,是携带药物或靶向吞噬体或感染部位的良好载体。如DP7是一种因为不良反应严重而不能全身应用的抗菌肽,可以通过阿奇霉素载入脂质体。在金葡菌感染时给与这些脂质体可以减弱DP7的不良反应,减少细菌负荷,减轻炎症。尽管有希望,目前临床上还没有应用杂交大环内酯类药物。
6.结论和展望
大环内酯类药物药物显著调节免疫反应,诱导促炎和抗炎效应,可以来纠正危重患者的免疫失衡。
大环内酯类药物的免疫调节效应复杂,受时间、记录和环境如病情严重程度影响。
体外观察到的一些效应可能阻碍大环内酯类药物的临床应用,如其可诱导淋巴细胞凋亡,以及MDSCs的扩增,两者都是免疫抑制的标志,增加危重患者继发感染的风险。
尽管如此,大环内酯类药物的抗炎和促修复效应可以减轻组织损伤,免于过度严重和细胞死亡,可能可以降低危重患者的病死率。
尽管可以利用其免疫调节效应,还缺乏临床证据。同时需注意其安全性,以及加重耐药性。
对于大环内酯类药物非抗菌效应的改进,可能增强其免疫调节效应。
xingxzh